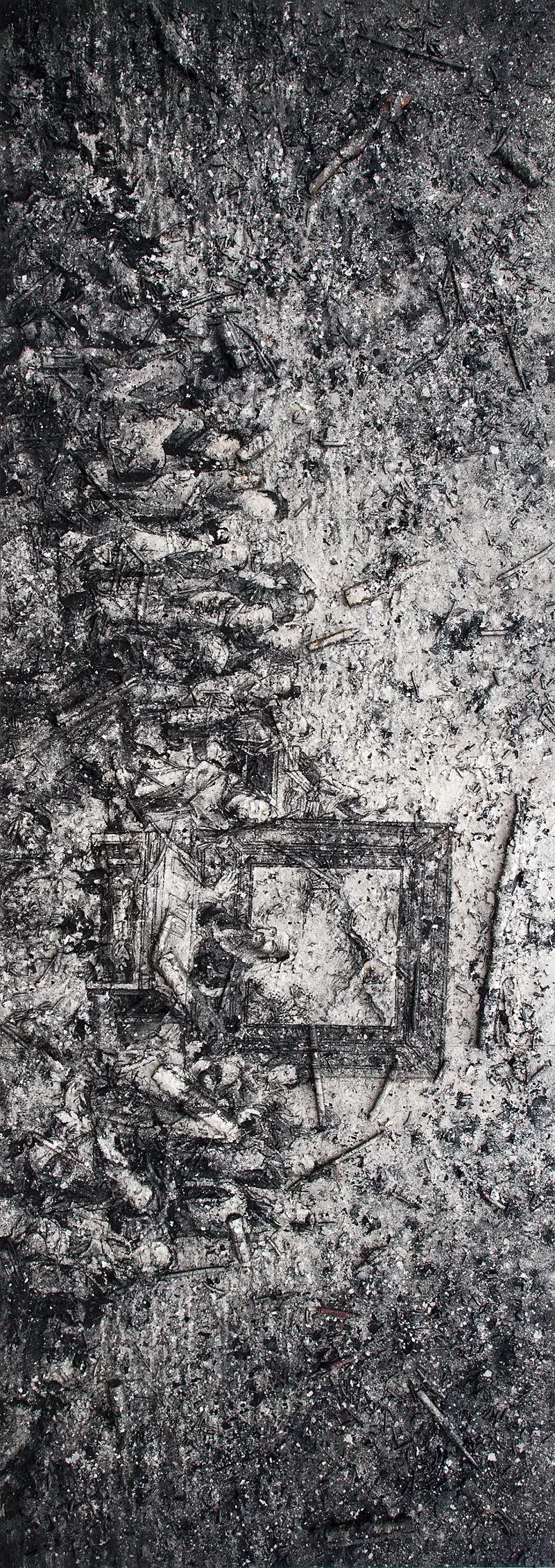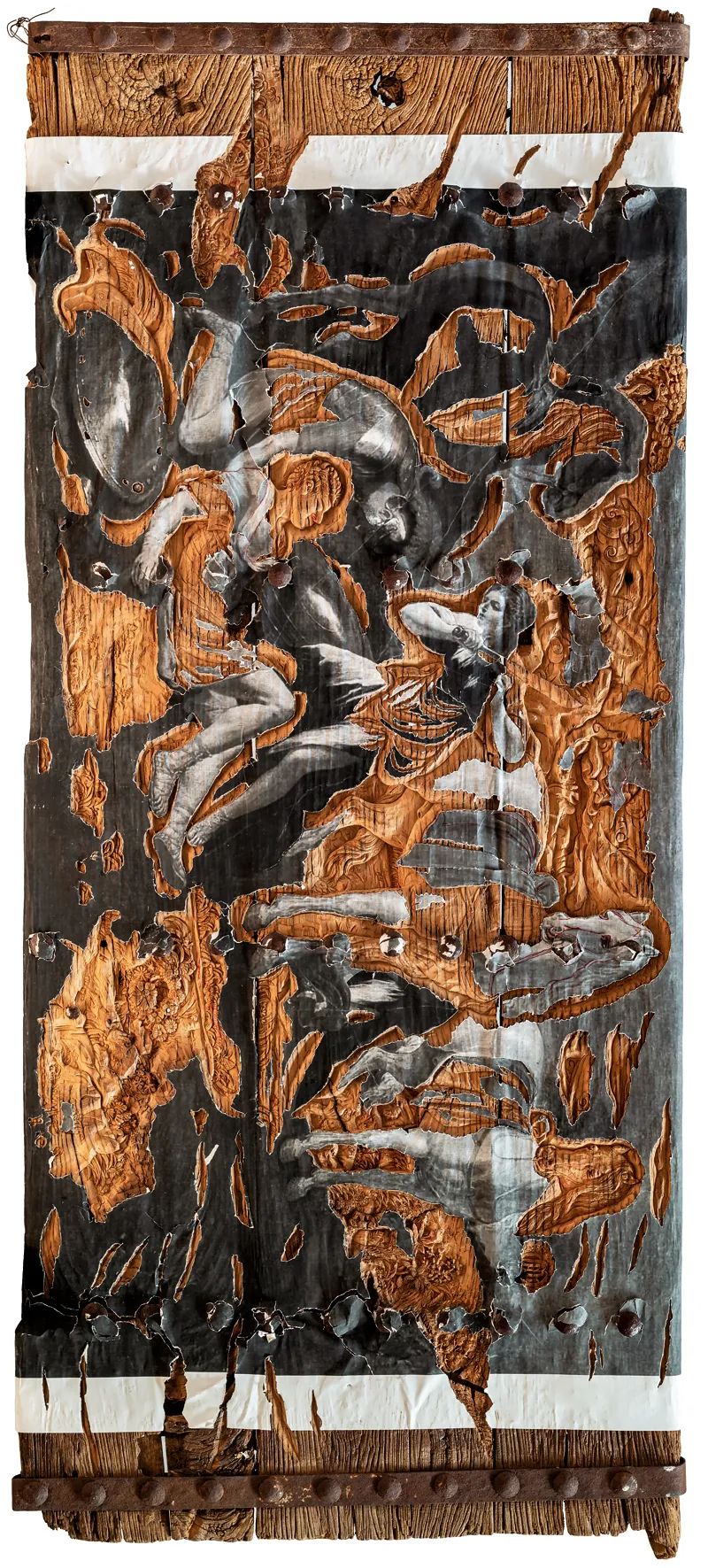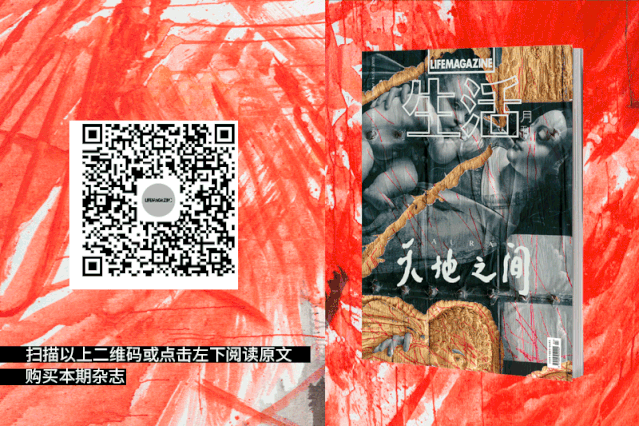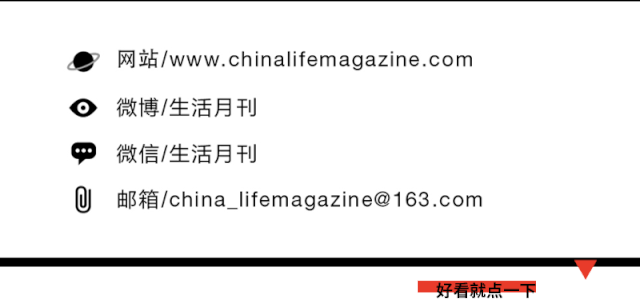手机App

版权家APP
扫描二维码
安装版权家客户端
小程序
-

微信小程序
扫描二维码
使用版权家小程序
-

百度小程序
扫描二维码
使用版权家小程序
公众号

版权家公众号
扫描二维码
进入版权家官方公众平台
微博

版权家官微
扫描二维码
进入版权家官方微博